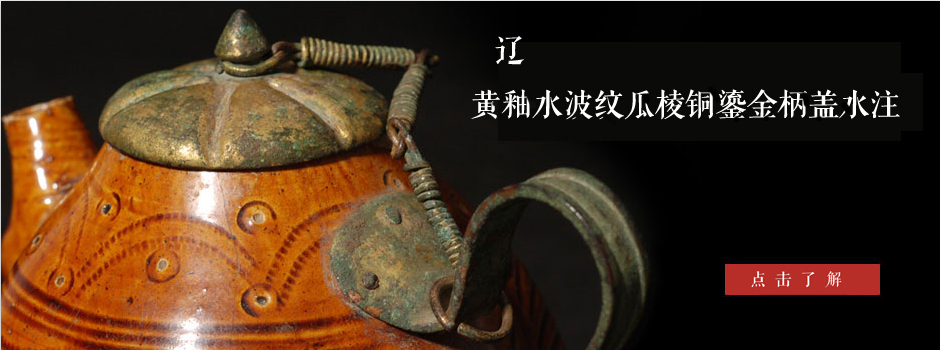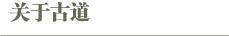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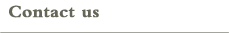
地址: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写字楼1座614-616
Tel:+86-10-65051177
Fax:+86-10-65058988
E-mail:soongs@soongsart.com
宋代官窑制度研究
南开大学历史系 刘毅
官窑制度是中国古代制瓷业发展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,官窑制度的实质是封建帝王凭借政治特权无偿占有优质陶瓷制品。官窑制度的形成,可以上溯到唐代越州的“贡窑”,即专门为唐朝皇室烧造贡瓷的窑厂,五代吴越时期,进而发展成为“设官监窑”,设官监窑虽不同于后代的官窑,但它却是由“贡窑”向官窑制度发展的桥梁,为官窑制度的形成作了准备。宋代是我们古代官窑制度的确立时期,特点比较鲜明。
一般认为宋代的官窑有汝官窑、钧官窑、汴京官窑、修内司官窑、郊坛官窑以及哥窑。下面分别介绍一下它们的情况:
(1)汝官窑:南宋人叶寘在其《坦斋笔衡》中有“汝窑为魁”的说法,汝窑是宋代最负盛名的窑口。传世宋代汝官瓷不足百件,它们的基本特点是:器型一般不大,胎呈香灰色,釉呈天青色,釉面有细碎的纹片,除个别型体较大者外,均采用满釉裹足支钉烧法。汝官窑窑址已在河南宝丰清凉寺找到,这里出土的御用汝瓷标本与传世品的基本待征完全一致。关于汝官窑的烧造时间,陈万里先生根据成书于宣和五年的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等有关文献分析,推断是在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徽宗崇宁五年(1086— 1106年)间,前后大约二十年。
(2)钧官窑:钧宫窑产品基本都是陈设用瓷,如各式花盆、花浇以及出戟尊、鼓钉洗等。胎色黑灰、质地坚硬,细致缜密。 钧官瓷的最大特点是其色彩鲜丽的窑变釉, 这种窑变为铜、铁等不同元素在烧成过程中自然流淌所形成,以红、蓝二色为主色调,有丁香紫、玫瑰红、天青、天蓝、月白等不同呈色,釉质浑厚,伴有“蚯蚓走泥纹”等特点,不少花盆底部还刻有一至十的数码字可以配套使用。钧官窑的窑址也已在河南禹县北门的钧台和八卦洞找到。钧官窑的烧造时间,李辉柄先生推断为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至宣和七年 (1101—1125年),前后约二十五年。
(3)汴京官窑:《坦斋笔衡》记载:“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,名曰官窑”;南宋人顾文荐在《负暄杂录》中也说:“宣、 政间京师自置烧造,曰官窑”。政和、宣和均为宋徽宗年号,当公元1111-1125年,这两项记载说明继汝官窑、钧官窑之后,朝庭又设置了一个汴京官窑。汴京宫窑瓷器的特点,文献记载语焉不详,无从得知,今人多认为与汝官窑相类,但釉呈粉青色,而且釉的纹片较大。也有人认为汴京宫窑不存在,“京师自置烧造”就是指汝官窑。
(4)南宋官窑:《坦斋笔衡》载: “中兴渡江,有邵成章提举后苑,号邵局, 袭故京遗制,贯窑于修内司,造青器,名内,窑,澄泥为范,极其精致,油色莹澈,为世所珍。后郊坛下别立新窑,比旧窑大不侔矣。”按照叶寘的描述,南宋官窑有两处,一处在修内司,即内窑,另一处在郊坛附近,即郊坛官窑。郊坛官窑已经在浙江杭州乌龟山发现,1930年中央研究院进行了调査试掘,确定了郊坛官窑的地望,1956和1985-86年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,获得了大量的实物材料。据介绍郊坛官窑可以分为早、晚两期,早期产品的主要特征是薄胎薄釉,通体施釉,色粉青,有开片,裹足支钉烧;晚期产品的基本特点是薄胎厚釉,柚层厚度普遍达到2毫米以上,系素烧瓷坯、多次挂釉烧成,玉质感很强,这类产品改用底足露胎的垫饼烧法,形成“铁足”。
另一处南宋官窑及修内司官窑,准确的窑址尚未发现,因而有人认为“南宋官窑窑址应该只有凤凰山南麓郊坛左右一个地带,别无所谓‘修内司窑址’的存在”。也有人提出一种新的看法,即认为修内司窑存在,但它不在杭州,而在龙泉,即“内窑”。郊坛官窑建于郊坛建成(绍兴十三年)之后,此前朝廷用瓷数目也很可观。我们不能因为万松岭一带(南宋修内司所在)找不到窑址,就否定修内司官窑的存在。
(5)哥窑:哥窑是宋代诸名窑中一个扑朔迷离的窑口,传世哥窑瓷器最大的特点就是开片,哥瓷纹片很多,大小不同,分深浅两层,经人工染成黑黄二色,俗称“金丝铁线”;哥窑瓷器的胎、釉特征有很大差 异,烧造方法也有支钉、垫饼之别,据此,冯先铭先生认为,传世哥瓷有南宋产品,也有些是元代产品,”以时间讲,其中应有出产早晚之别,从产地说,也恐非一个瓷窑的出品。”也有人认为传世哥窑瓷器多数是元代烧的。浙江龙泉窑发现黑胎青釉开片瓷以后,使问题更加复杂,但龙泉这种黑胎开片瓷与传世哥瓷差异很大,周仁等先生经过化学测试得出结论:“传世宋哥窑不在龙泉烧造之说是可以接受的”。李辉柄先生认为,传世哥瓷是宋代官窑产品,应该把它和龙泉哥瓷区分开来研究,后者是民窑产品。笔者认为,那些确认厲于宋代的哥窑瓷器是宋代某个官窑的产品,而龙泉黑胎青瓷则是民窑仿官产品,二者不存在重合关系。龙泉地区方言,“官”、“哥”二字发音恰与别处颠倒,当地人读官音“gē”,与旁处“哥”相类,仿官(gē)窑径称为“官(gē)窑”,后讹为“哥”,这种可能性很大,所以明代又有了章氏兄弟生一、生二各主一窑的传说,遂有“哥窑”、“弟窑”对举,把后人寻找“哥窑(官窑瓷器)”窑址的视线引向龙泉。传世官“哥窑”的产地,目前尚难确认,明代笔记《广志绎》中透露一些线索:“官窑品格,大率与哥窑相同”,“窑在凤凰山下”,“哥窑烧于私家,取土俱在此地”,据此说传世“哥窑”也出产于浙江杭州凤凰山。另据传世宋“哥瓷”黑胎、粉青釉、开片等特点与郊坛官窑产品相似,而且部分“哥瓷”质地明显优于郊坛官瓷、装饰风格更近于汝官瓷的事实,笔者妄断,传世宋“哥瓷”的窑口与所谓 “修内可窑”在时间和地点上有重合关系。
宋代官窑烧造制度比起明朝早期来还不够严格,官窑制度还处在它自身发展的早期,宋代是中国古代官窑制度的确立时期,具有如下基本特征:
(1)官窑制度的确立,根源于宋皇室对优质瓷器的大量需求。瓷器自东汉末年正式烧成以来,一直是民间主要的日用器皿,充作宫廷御用,则要晚些。文献和考古材料证明,唐代已有瓷器贡入宫中。到北宋,朝廷更广泛地接纳各地进贡的资器,据宋代文献如王存《元丰九域志》、庄绰《鸡肋篇》、 叶寘《坦斋笔衡》、赵与吋《宾退录》以及 《宜和遗事》、《宋会要(辑稿)》等记载,宋代的几大名窑越窑、定窑、耀州窑、 汝州窑、景德镇窑、建窑、龙泉窑等都曾向朝廷进贡瓷器,这些记载已基本为考古发现所证实。在北宋都城汴京,设有专门收藏这些贡瓷的“瓷器库”。“瓷器库,在建隆坊,掌受明、越、饶州、定州、青州白瓷器 及漆器以给用”。由于质地日益精良,瓷器加入到帝后日用器皿行列,河北定窑法兴寺窑址中出土过刻有“尚食局”、“尚药局”铭款的白瓷标本,按宋代尚食、尚药两局均隶属于殿中省,其职掌是“监掌供奉天子玉食、医药、服御、幄帟、舆辇、舍次之政令”,刻有这二局铭款的瓷器应专为供奉皇宫饮膳、用药而烧造。北宋晚期的宋哲宗更室“饮食皆陶器而已”。这些日用瓷器还作为殉葬品入葬帝后陵中,供其阴间享用,如袝葬宋太宗永熙陵的元德李皇后陵中即随葬大量瓷器,此陵虽曾被盗,但在清理发掘中还是出土了优质越窑秘色瓷三件、精细的定窑白瓷三十七件,主要造型为盘、碗、杯以及套盆等。由于一般窑场的生产,无论从质量上、数量上都无法满足宫廷的大量需求,特别是为了保证供御品的精益求精,官窑制度便应运而生。叶寘《坦斋笔衡》中“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,不堪用,遂命汝州造青窑器”的记载虽带有片面性,却正是这一转变的真实反映。
(2)宋代官窑的生产目的,是为了满足皇室需要,因而生产技艺精工,不计原料、成本价值。据南宋人周辉《清波杂志》记载,“汝窑宫中禁烧,内有玛瑙为釉”清凉寺发现的汝官瓷标本,开片呈鱼鳞状,即纹片之间断面为一个斜面,首尾相叠,在30倍显微镜下观察,可见釉中气泡如油滴状,有些地方还有银星点,承何南省文物研究所赵青云先生见告,此即系玛瑙结晶所致。为了保证汝瓷呈色和纹片的佳丽,便把经济价值较高的玛瑙入釉料中,只有实力雄厚的官窑才能长久为之。钧官窑等官窑的设立也都能说明这个问题,传世的钧官窑瓷器基本都是用于陈设的花盒、奁、出戟尊、鼓钉洗等,供皇宫陈列花木奇石用。据分析,钧官瓷的生产与宋徽宗“花石纲之役”有关:“河南禹县的钧台窑就是为了适应宫廷的需要,从民间集中了一些优秀的工匠,专烧宫廷陈设用瓷,这就是钧窑之中官窑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时代背景”另外,南宋官窑中厚釉一类产品,须经多次挂釉才能烧成,它的持续生产,也须有强大的经济后盾。官窑瓷器按照宫廷设计的样式进行生产,上举宋代汝官、钧官所烧陈设用瓷均属此类,特别是钧官窑各式花盒底部的汉字数码,用来标记样式尺寸,更可以证明这一点。官窑瓷器不仅要严格按设计生产,而且产品质量必须精益求精,稍不合格,即须就地打碎重新烧造。宋代的几处官窑,都设在京城附近,有些就在京城内。例如汝官窑、钧官窑同在京西路,后者更近于汴京,至于文献中记载汴京官窑、修内司官窑和已经找到窑址的郊坛官窑更是直接设在了京师。从汝官窑到京城官窑的发展,不仅是地理方位的转移,而且反映了宫廷对官窑控制的进一步严格。
(3)宋代官窑由朝廷派人管理。关于主持官窑烧造的政府机构,文献记载比较模糊,应该是几种可能性并存的。从《坦斋笔衡》“置窑于修内司”一语来看,似乎与修内司有关。按《宋史.职官志》,修内司为将作监下属机构之一,“掌宫城、太庙缮修之事”,并无烧造瓷器的职责,可能与瓷器有关的,倒是将作监的另一个下属机构------“窑务”,它的职掌是“掌陶为砖瓦,以给缮营及瓶缶之器”傅振伦先生曾有“命将作少监萧服在汝州监督瓷窑务”的说法,只是不详材料所出。除将作监外,文思院和后苑造作所也是值得注意的机构:“凡进御器玩、后妃服饰、雕文错彩工巧之事,分隶文思院、后苑造作所”。前引《坦斋笔衡》中“提举后苑”之说,“后苑”除了作为专用名词即“皇宫后花园”外,还可以理解为官府名称,即后苑造作所,与“提举”二字联用,后者可能性更大,因此,我们不能忽略后苑造作所主持官窑烧造的可能。按照南宋人吕祖谦《官箴》的记载,宋代官窑窑场还设有监窑官,“有为京西转运使者,一日间监窑官:“日所烧柴凡几灶?”曰:“十八、九灶”。曰“吾所见者十一灶,何也?”窑官愕然”。转运使“掌经度一路财赋,而察其登耗有无,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,岁行所部,检察储积,稽考账籍,凡吏蛊民痪,系条以上达,及专举刺官之事”,因此有权向监窑官询问烧造情况。按宋代京西路包括今开封以西河南以及湖北北部地区,分南北两路,南路设襄阳府,邓、随、金、房、钧、郢、唐七州和光化军,北路设河南、颖昌、淮宁、顺昌四府和郑、滑、蔡、汝五州及信阳军。汝官窑和钧官窑正在辖区之内。由于官窑的开设多是临时性的,朝廷派政府官员管理固然可以,也可以随时设立一些临时性机构主持窑务,更可以利宦官。宋徽宗对奇花异石、古董珍玩特别喜好,派宦官四处设局插括,杨戬、李彦、等曾“设局汝州”
很可能插手窑务。至于两京官窑,与皇宫相距迷迩,派宦官主持更在常理之中。“邵成章提举后苑”之说虽不足凭信,但却透露了宦官曾主持官窑(至少是南宋官窑)烧造的史实。事实上,造作所本身就是宦官机构。
(4)宋代的官窑虽为皇室需要而生产,并由政府派官员专门管理,但当时的官窑制度还不像明初那样禁令森严。《清波杂志》说:“汝窑宫中禁烧,内有玛瑙为釉”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,近尤难得”。按照他的记载,汝官瓷虽严格控制烧造,“宫中禁烧”,但除了“供御”的正品外,余下残次品有些尚可出卖。南宋绍兴二十一年(1115年)十月,宋高宗临幸清河郡王张俊府第,张俊曾贡献汝瓷十五件,即酒瓶一对、洗一、香炉一、香盒一、香毯一、盏四只、盂子二、出香一对、大奁一、小奁一。张俊这些汝瓷的来源有两种可能,一是先朝帝王所赐,再是购买了供御拣退的变价品。如是前者,须加特别说明,否则会被视为大不敬,所以应属于后者。另外,在北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一汝官盘和汝官碟,底均刻有一“蔡”字,据分析,此铭文为物主姓氏,物主可能蔡京或蔡绦父子,他们或位及人臣,或贵为驸马,有可能被皇帝赏赐汝瓷。但在御赏器物上刻划姓氏,难免冒犯皇帝尊严,所以这两件器物极可能是蔡氏所购的供御拣退品。汝官窑残次品的出卖,反映了官窑制度在其初期阶段尚不甚严格。即使如此,出卖的汝瓷数量也很有限,价格也会特别昂贵,所以在宋代墓葬中至今没有发现。在宋代文献中还没有能够发现关于钧官窑、两京官窑瓷器变价出卖的记载,目前也没有找到考古学上的证据,看来宫廷对于它们的控制更要严格一些。另据元末成书的《静斋至正直记遗编》中有“近日哥窑绝类古官窑,不可不细辨也”之语分析,元末世间是可以见到宋官窑瓷器的,但这些东西究竟是南宋变价的残次品,还是宋亡后逸出宫禁抑或盗发宋帝陵寝所得,尚难以判定。
(5)宋代官窑出现的技术基础是河南地区制瓷业工艺水平的迅速提高。从唐末开始,河南再度成为全国第一政冶中心,五代和北宋先后定都开封,更加巩固了它的地位。作为京都,河南地区的手工业也由于各种条件的作用,迅速发展,陈万里先生即认为,吴越国不断向北方进贡秘色瓷、使河南青瓷制造业受到影响,促进了它的发展,其中佼佼者汝官瓷,就是“受着南方越窑秘色瓷的影响”而发展起来的。北宋晚期,河南青瓷已经取代了越窑青瓷独占鳌头的地位。据《元丰九城志》记载:北宋朝廷每年接受贡瓷三百一十件,其中河南二百,耀、越各五十、邢十,可见河南青瓷质量之高。到了北宋晚期,又以民窑烧造技术较好的窑口为基础,先后建立了汝官窑和钧官窑。宋代两京官窑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窑的影响,郊坛官窑除受北方窑系影响外,还受到南方龙泉窑的影响。宋代官窑与民窑的关系,不像明初那样截然对立。初立的宋代官窑烧造制度还不十分严格,并没有把皇宫用瓷与民间用瓷的生产彻底分开,已调查发掘的汝官窑、钧官窑除官式青瓷外,都还有其它产品出产。清凉寺汝官瓷“宫中禁烧”以后不再允许民间生产天青釉一类产品,民窑只能生产耀州窑系的青黄釉瓷(即临汝瓷)以及宋三彩、白地黑花碗、盘、黑釉兔毫盏、酱釉罐等,“民用器占90%以上,御用汝瓷比例很小”。钧官窑窑址上,“还有一定数量的汝瓷、天目瓷、白地黑花民用瓷等”,“在烧造时有着明显的分工”。这说明,在为皇室进行官窑生产的同时,不同于官样瓷器的民间用瓷也在附近烧造,除官样瓷器被严格限制外,并不禁止民用瓷的生产,由于官窑开窑时间短,窑工很可能有穿插现象。两京官窑地近大内,更直接效力宫廷,不再象汝官窑、钧官窑那样与民窑栉比相次,变得神秘莫测。但到少在南宋时期,官窑产品的风格又对龙泉窑产生了影响,一般认为龙泉窑出土的黑胎青釉开片一类标本即是仿官产品。冯先铭先生认为:“龙泉黑胎青瓷正是《格古要论》指出的乌泥窑,是仿官的作品,器物造型与杭州乌龟山官窑出土的标本有不少共有的式样,说明与官窑有着密切的关系”龙泉仿官产品与官窑产品显然不同,但在青釉、黑胎、开片等方面却做到了相似,这表明,南宋时期民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模仿官窑产品的特征。